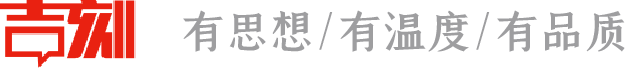引 言
查干淖尔大草原浩荡无边,肥沃的黑土地上似乎永无休止地生长着齐腰深的小叶章草,草原狼似乎也永无休止地在翻滚的草浪中匆匆隐现。奔腾的霍林河水由西向东横贯草原中部,河水季节性汹涌咆哮时,常常伴随着狗鱼群血红色的怒吼声。天性凶猛的狗鱼群总是追杀着草鱼群而来,它们对草鱼群就像怀有千古的仇恨,一路掏咬撕扯,生吞活剥……最后,那怒吼声伴着腥红的霍林河水渐渐低沉而去,直至淹没到远方浩瀚无边的查干湖深处。拉嘎老古庙里吟诵的喇嘛经从来没有停歇过,沙哑的皈依颂文犹如雄浑的蒙古族长调,偶尔也夹杂着几声粗俗的草原民谣,哼哼呀呀的和声一直萦绕着草原上大大小小的敖包子随风飘荡……
查干淖尔大草原深处的塔头滩上,苇草丛生,湿地成片,就更加显得广袤而神秘。夏天,一野碧绿;冬天,满目苍白。我永远都无法抹去塔头滩留在童年记忆里的深刻烙印,草原风掀起一拨又一拨浩荡草浪时,总能让我联想到马群的脊背,牛群的脊背,羊群的脊背,甚至是狼群的脊背……最后这些脊背奔涌成血味十足的红色肉浪,翻滚的草浪间时隐时现的塔头墩子就像一群群黑色妖灵,一直在辽阔的查干淖尔大草原上纵横驰骋……
我还是个咿呀学语的孩童时,塔头滩就铁青着面孔向我宣布了:“王龙飞!你给我听清楚了!这里是强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地盘,这里的一切都属于强者!小兔崽子,当心你的小脊梁骨,还有你的小嘎拉哈!”似乎从那时起,我就懵懵懂懂并根深蒂固地认识到:这里的女人是属于强者的,尤其是美丽的女人一定要属于强者。弱者不仅得不到女人的爱情,更得不到女人的身体,连娶个最丑陋的女人繁衍后代的机会都没有。直觉还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上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理解:一个男人猎取美丽女人的能力就是他的生命能力和生命价值。这种畸形的理解一直伴随着我以后的生活,甚至在我后来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文明教育后,那种牢固的洪荒印记也一直没有从我内心深处淡化出去。耳畔至今仍回荡着我儿时的真心呐喊:“等着吧,别他妈老用那种眼光瞅着我。终会有一天,塔头滩上的美女会任我王龙飞随便挑选的!”至今,那乳臭未干的喊声仍然真挚而清晰地回荡在我的耳畔……
塔头滩冬猎队这个名字更是渗入到了每个人的骨髓,它一直以判官的形象把塔头滩人分为两类——强者与弱者,或者说英雄与狗熊。前者上天庭,后者下地府。在塔头滩人的心目中,能入选塔头滩冬猎队就能拥有一切,塔头滩冬猎队要比历史上任何国家的任何王牌军队都神圣得多。在人们不太知道外面世界,或者知道一点儿也不放在眼里的塔头滩,冬猎队的崇高程度绝不亚于诺曼底登陆的二战盟军,冬猎队队长的自我感觉就更是无比良好了。如果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拿破仑、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巴顿等将军,也绝不会感觉自己有半点儿逊色的。我曾以幼小的塔头滩平民的身份体验过塔头滩冬猎队的荣耀与辉煌。直至今天,我一回忆起塔头滩冬猎队,它仍然能让我无条件地肃然起敬。虽然我早已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乌合之众,那都是些什么荒野草民,但我还是无法阻止自己。时至今日,一提起塔头滩冬猎队,我仍然不由自主地诚惶诚恐……
我还由衷地怀念那些飘着粘乎乎的长头发、光着红彤彤的大膀子、提着光闪闪的“掏捞棒子”从草原上拍马喊过的猎手们,怀念那些马匹身上散发着的那股子浓烈的汗腥味儿和尿骚味儿,怀念猎手们那略带残酷的傲慢喊声,也包括他们说话时经常夹带出来的劲道脏口。虽然狼群和鱼群始终残酷无情地评判着人群,虽然人群的浴血竞争直接导致王氏家族沦为底层弱民,但我还是无限崇敬曾让我苦难压抑、让我撕心裂肺的塔头滩和滔滔不绝的霍林河。那里虽苦难,但很真实;那里虽残酷,但很公平。
在人们的常规印象中,大草原通常应该是碧绿色和墨绿色的,或者有时会是土黄色的,顶多也就是灰褐色的,但在我根深蒂固的童年记忆中,不仅仅是塔头滩,就连整个查干淖尔大草原都是红色的。无论春夏秋冬,大草原一直都是红色的,并且永远都是红色的,宛如一头巨大无比的红发魔兽……
1
伴着亘古传唱的皈依颂文和草原民谣,草原风永不停歇地刮着。草原风刮过碧波荡漾的查干湖,刮过草浪摇曳的西大洼,刮过无边无际的塔头滩,刮过神秘莫测的鸡爪壕……除了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蒿草味,一路上还裹挟着苦嗖嗖的野花味和咸丝丝的汗腥味,有时还夹杂着温吞吞的马牛羊等食草动物粪便的柴腐味,或者是热乎乎的狼狗猫等食肉动物粪便的酸臭味,那是每个塔头滩人都熟悉的草原上特有的复合气味。那气味一点儿都不难闻,对于塔头滩人来说那是最让人心安理得的气味了。甚至可以说,那是草原上亘古不变的别样芬芳。浑厚浓烈的气味穿过河流,穿过草地,穿过我困惑而迷茫的整个童少时代……
谁也说不清从什么时代起就有了这群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杂居的剽悍民众。也许是从满清入关,康熙东巡?从岳家军高举长矛,直抵黄龙之时?还是从薛礼东征,抑或是北方高句丽王朝雄壮崛起的那天开始?总之,在很久很久以前,塔头滩就成了角力厮杀的圣地,就成了繁衍剽悍的地方。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不管又来了哪个民族的人群,都一概被这里既有的勇猛之伍所洗礼、所同化,让不屈之魂渗入到每个生命的血液和骨髓深处。然后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生存氛围──所有的男人和雄性必须首先告别任何形式的懦弱才有资格在这里生存。也许就是从某个遥远的年代起,塔头滩人世世代代就一直抖擞着这股与众不同的雄风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与众不同的强硬风格,才造就了包括我们王氏家族在内的塔头滩上很多家族的沉重和好强。他们疼痛着,他们隐忍着,他们挣扎着,他们梦想着……
塔头滩人从来不把那些手提猎枪、百发百中地将远处飞奔的野兔撂倒的猎手视为优秀猎手;塔头滩人也从来不把那些抛圆大旋网、一旋网打上几十斤杂鱼的渔人视为上等渔人。人们把最受尊重的猎手称作“汉哥”,把最瞧得起的渔人叫作“把头”。草原上真正的“汉哥”从来不使用猎枪。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提着一根两尺余长的“掏捞棒子”,腰里别上一把羊角剃刀。“汉哥”对野兔、野鸡等小猎物看都不看,他们只对查干淖尔大草原上最凶顽的猎物──草原狼感兴趣。他们斗狼的方式也极其独特,先凭勇猛使狼被动逃跑,然后再与狼拼耐力斗智力。称得上汉哥的猎手从来不找狼的短处,他们愿意看到凶恶的草原狼施展完浑身解数后俯首认输,这时他们才伸出大手揪住狼的后背将其擒到马上。草原上真正的“把头”从来不用网,他们仅凭一柄锈迹斑斑的黑色钢钩和一双有力的手臂来对付霍林河里最霸道的巨型狗鱼。常常要和垂死挣扎的巨型狗鱼滚作一团,拼个你死我活……印象中,好像只有那些不成年的半大孩子和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才用渔网去网鱼,才下挂子去挂鱼。
纵横大草原多少年了,塔头滩汉子的标准装备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一个套马杆子,一根“掏捞棒子”和一柄羊角剃刀,没有人见过同时身上又背着一杆猎枪的塔头滩汉子。
在塔头滩,能被尊称为“汉哥”的人并不多,同时又被尊称为“把头”的人就更显得凤毛麟角了。因为任何领域里做到真正的英雄都是不容易的,跨领域再做英雄则更是难上加难。既当“汉哥”又当“把头”,其难度起码也要相当于今天NBA赛场上的全能战士,或者网球场赛上的大满贯选手。塔头滩人在这些问题上从不含糊,他们的眼里也从来容不得沙子。塔头滩人把既是“汉哥”又是“把头”的草原汉子亲切地称为“草原红鹰”,更是加倍敬重,并对他们给予无条件的厚爱,给予他们能够给予的一切……
塔头滩从来不缺少筋肉与利齿的残酷较量。草原狼这个名字叫得最响亮时,也正是草原狼群最兴旺的时候。草原狼群昼夜用绿色的眼睛威慑着草原人及属于草原人的一切可供充饥的肉身。在草原狼群的包围下,塔头滩上平凡的百姓有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为了使事业更像事业,后来又有了塔头滩冬猎队及其狩猎规则。于是,有了强者和弱者,有了英雄和狗熊,又有了美女们更隆重、更惊艳、更合理的分配原则……
霍林河里鱼群之间的弱肉强食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有时,表面看上去非常残酷无情,实际上则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日常规律。凶猛的狗鱼群一路追杀着草鱼群而来,杀气腾腾、生吞活剥,看上去血腥,但从本质上看,那又是一种最博大的慈悲。霍林河里的草鱼群就像草原上的羊群一样,一旦更多的草鱼群进入查干湖,查干湖就会失去应有的生态平衡。由于食草鱼太多,最后就可能导致湖里所有的鱼都无食可吃,甚至会因为严重缺氧而全部窒息而亡。所以说,狗鱼群的生呑活剥就变得极其必要。反过来说也一样,狗鱼多了不行,没有狗鱼也不行。尽管狗鱼是专门吃鱼的大型肉食鱼,但草原人也从不对他们斩尽杀绝,因为狗鱼和草原狼一样,都是草原生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每年的七八月份,就是霍林河激情澎湃的汛期。霍林河水在这一季节异常汹涌,像脱缰的烈马一样,一路奔腾咆哮……为了食物,鲫鱼群、鲤鱼群、鲢鱼群、草鱼群、鳙鱼群等在这个季节都要逆水洄游,它们一拨一拨地顶水北上,狗鱼群、鲶鱼群、黑鱼群等食肉鱼群就一拨一拨地尾随而来,狗鱼群最凶残,它们一路追杀,发出的怒吼声搅浑了猩红的河水。天空中白色的打鱼郎也一路跟随而来,因为鱼群经常被追得跃出水面,打鱼郎一个俯冲就能叼住它们最想要的美味……霍林河水一度就被搅和得狼烟四起,血味十足。半个多月以后,突出重围的鱼群才能最终抵达那浩瀚无边的查干湖深处……从此过上相对平稳安定的日子。
钓巨型狗鱼,当传世“把头”。在闷热难奈的夏日,塔头滩人又有了另一项轰轰烈烈的事业……
塔头滩上著名的拉嘎老古庙就是为世世代代的“汉哥”和“把头”们修建的。祖母说不清老古庙的始建年代,也说不准老喇嘛乌兰巴布的年纪与身世,拉嘎老古庙实在太古老了。喇嘛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喇嘛是上师,上师得悟于大菩提,与虚空法界合一,与芸芸众生合一,与依止根本上师合一,那才有资格做上喇嘛。
拉嘎老古庙里供奉的不是神仙鬼怪,也不是帝王将相。塔头滩人把每年猎到的最凶最猛的头狼毒牙和每年钓到的最大最长的巨型狗鱼头骨悬挂在老古庙里。塔头滩人认为征服草原狼和巨型狗鱼靠的是同一种东西。他们没有说出的那种东西就是勇气、力量和智慧。实际上,头狼毒牙和巨型狗鱼头骨就是勇气、力量和智慧的象征。它们一直充当着草原人虔诚跪拜的图腾,使每块骨头都蕴含着塔头滩人不止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后来,塔头滩人又创建了一支专门对付草原狼的冬猎队——塔头滩冬猎队,能入选为冬猎队队员曾一度成为塔头滩男人的骄傲和梦想。实际上,关于塔头滩人夏天捕巨型狗鱼、冬天猎草原头狼的记录,就是塔头滩人再精确不过的历史了。
天长日久,草原狼群和巨型狗鱼越来越演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凝重符号,渗入到每个塔头滩人的骨髓,塔头滩人已逐渐无法接受也无法想象没有草原狼群和巨型狗鱼的日常生活。总之,塔头滩早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境界,那是查干淖尔大草原、霍林河水、人群、狼群和鱼群们同生共存的命运哲学。
真正的塔头滩汉子不仅打狼和钓鱼行,骑马、射箭、杀牛、宰羊……样样都得行。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族在塔头滩的生活一直是苦难的。从我记事起,我王氏家族在草原上出演的都是悲剧。祖父率领着他的儿孙们一直在呕心沥血地为成为“汉哥”和“把头”而艰难奋斗着。他们身负重荷,匍匐挣扎在众多强手的脚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始终没能如愿……
2
飘忽不定的雄云雀总是突然间就没了踪影,只留下悦耳的歌声;哪怕是最嘈杂的清晨,黄鼠子和野兔子们也能听见一片片、一圈圈的花脸蘑和狗尿苔们破土而出的声音……
除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和间接感悟,我对塔头滩的认识更主要是来源于祖母的讲述。尤其是在我记事之前,我对大草原及塔头滩冬猎队的认识基本上都是从祖母那里获得的。哪怕是讲到王氏家族的耻辱,祖母也从不避实就虚,更是拒绝文过饰非。祖母总是给我讲述那些真实地发生过的事情,发生在老王家人身上的故事总是尴尬多于体面、耻辱多于光荣。祖母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至今仍然完好无损地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祖母肯定是塔头滩上的一个独特例外。我偷偷端详过祖母那依旧秀气的脸颊,常常暗自揣摩:谜一样的祖母当初为什么选择下嫁给身体残疾的祖父呢?各方面都那么出色的祖母为什么没有嫁给大英雄胡老五呢?胡老五当年为什么大操大办地娶了小蛮腰(孙三美,也就是后来的老胡五奶)呢?老年的祖母和老胡五奶正面接触不多,偶尔见面也总是点头微笑一下,总是保持着以礼相待的距离。我一直想知道,祖母年轻的时候和小蛮腰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纠结?她们之间有着哪些故事呢……
我记事时祖母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眼中的祖母当然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祖母。我的印象中,平时一脸威严的祖母和老胡五奶见面时却总是客客气气的,那种客气绝不是寻常的两个老年村妇邻里间的简单客气,而是一种骨子里较着暗劲儿的复杂客气。她们之间肯定有着许许多多无可言说的微妙关系。对于这些,我一直无从得到标准答案。有时我反倒觉得,祖母本身就是查干淖尔大草原谜一样的存在。
祖母出身于中医世家,是塔头滩上少见的有修养、有文化的女性。塔头滩上有四百多种野生花草都具有药用价值,祖母竟能根据花草的不同品性,搭配出治各种病的中草药来。别的我忘了,我只记得祖母自制的刀口药就特别好使:每次手上划了口子,敷上之后不仅能立刻止血,还能马上止疼呢。
据说祖母小时候还读过《论语》和《史记》呢,她对草原上流传的历史故事和草原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也很感兴趣,有关王氏家族的故事就是祖母一边做家务活儿一边讲给我听的。从我记事开始,祖母就没停止过对我的耐心教诲。祖母除了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人为镜,以史为鉴”等文词,也常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好汉不提当年勇”等土词。她经常说的另一句土词是“叫唤雀儿没肉吃”,成了她调教我的口头禅。祖母说话声音并不大,总是和声细语的。哪怕是在我犯了错误的时候,祖母也从来不直接教训和批评我,只是表情严肃地跟我讲道理。祖母说话也并不是多么的生动,但总是柔和中带着刚强。就像字字板上钉钉,句句真实可靠,谁听了都会感到不容置疑。尤其是祖母的那双眼睛让我永生难忘,那不仅是一双美丽善良的眼睛,同时那也是一双不容苟且的眼睛……
(转载内容已由作者授权,转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血色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