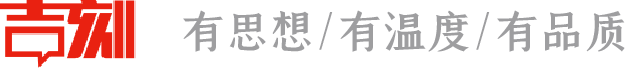作家 王怀宇
《血色草原》是我最看重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前我总是说自己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是“这一部”。2019年12月《中国作家》曾以《红草原》为题全文刊发了这篇小说,但那时还只是第6稿,只有20万字。以后的一年里,我前前后后又修改了6稿,尤其是第12稿,我听取了文学评论家胡平、孟繁华、王春林和责任编辑史佳丽等老师对第11稿的阅读意见后进行修改,这才有了这部35万字的最新版本的《血色草原》。
1994年,我就以草原为背景创作出了《家族之疫》和《狼群早已溃散》等中、短篇小说,之后的一些年里,文学同行们纷纷向我建议,希望我再以东北草原渔猎农耕生活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拥有的素材还远远不够,还不足以支撑我去书写一部长篇小说。以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有关草原题材的小说我只写了一个,那就是短篇小说《北方往事》。
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虽然一直没有动笔去写那部长篇小说,但是,要写一部关于东北汉人草原的长篇小说这件事已悄然成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巨大情结。一直以来,我好像总是在心里和自己较着一股劲:不写则已,要写就写出不同的。要写出不同于内地旱草原小说,要写出多民族同生共融的水草原小说。我希望写出淳厚丰富的人生况味,凝重深沉的历史轮回和复杂多变的生命关系。随后的阅读中,我也格外关注那些写狼写草原的优秀作品。与其说我是在学习,不如说我是在绕开。我想,如果我写的草原、大河和狼群与人家写的相类似,那么我的书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述着草原的故事。父亲讲述的草原,绝不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更多的好像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豺狼”。总是充满着无穷的神秘感和巨大的生命力,故事中的东北大草原永远都是碧浪滚滚、草长莺飞……
为了求学,我七岁就离开了草原。
而当我再次回到草原时,眼前的草原就像换成了另外一块草原。原上草越来越低矮、越来越稀疏,飞禽走兽也并不常见,狼已变成了传说……尤其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别说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了,就算是风不吹、草不低,站在远处都能看见一只黄鼠子在忐忑不安、踉踉跄跄地奔跑着,来到近处,地上的草连鞋面都盖不住了。
毋庸置疑,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草原退化了,河流萎缩了,狼群消亡了……但我对草原依旧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决定找回童年记忆中的那块草原。于是,我只好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想象我的百年家族,还原我的坎坷童年……
1989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吉林省群众艺术馆工作,这里有着群文人的事业,平静如水的生活中同样不断绽放出欢快与伤痛。从一本大众杂志的助理编辑做起,几乎一步不落地做遍了所有的角色,一干就是二十四年。
2013年,我被调到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当副院长,主抓全省舞台艺术创作。同样面对那些看似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但也能让我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欢快与伤痛。有些东西就是说不清、道不明,只能深藏于内心。同时,我也充分体验了一次悲剧喜唱式的戏剧人生。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写成我那关于东北大草原的长篇小说,其间却写了另外两个反映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漂过都市》和《心藏黑白》。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草原。活生生现实总是让我回想起草原上那些英雄和弱民。为了冥冥中那部关于东北草原的长篇小说,我还是对习惯性地以各种方式关注着家乡草原。我经常有意去家乡草原采风,因为是带着问题去的,所以每一次感触都非常深刻,也就不断积累起了更多的创作素材。二十四年的群众文化工作让我先后来到五十余个草原乡镇进行过调研,又积累了其他一些有关草原的素材。
我为什么要写《血色草原》?不仅是因为我对童年印象中的草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更是因为我对现实中渐渐远去的草原的一种焦虑和痛心。
为什么是血色草原?那绝对是我根深蒂固的童年印记。草原通常应该是嫩绿色和墨绿色的,或者有时是土黄色的,顶多也就是灰褐色的,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草原是红色的,更是血色的。无论春夏秋冬,它一直都是血红色的,并且永远都是血红色的……草原风掀起一拨又一拨的浩荡草浪时,总能让人联想到马群的脊背,牛群的脊背,羊群的脊背,甚至是狼群的脊背……那也分明就是汹涌着的血红色肉浪。
有人说,《血色草原》是东北草原的风俗画卷,是强者基因的血性史诗。不仅是草原汉子骁勇猎狼的洪荒故事,更是人群与狼群同生共存的命运哲学。但在我这里并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草原最可贵之处就是——那里虽苦难,但很真实;那里虽残酷,但很公平。
2015年7月,为探求东北草原与内蒙草原的区别,我还来到乌拉盖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此行让我感受到,内蒙的旱草原和东北的水草原确实有着巨大差异和诸多不同。
东北草原上的塔头滩人奉“猎狼不使刀枪”、“捕鱼不用渔网”为至尊,这里所发生的洪荒故事与众不同。王氏家族在塔头滩的生活一直处于顽强抗争状态。从祖父那代起,王氏家族一直上演着失败者的悲剧。祖父率领他的儿孙们一直在呕心沥血地为成为强者而奋斗着,他们身负重荷挣扎在强者的脚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不能如愿。但王氏家族还是无限崇敬让他们苦难压抑的塔头滩,顶礼膜拜让他们撕心裂肺的霍林河。而缔造王氏家族后人们一系列苦难的人又恰恰是王氏家族自己的一位先辈……作品还书写了人类情感生活的位移、人类竞争方式的演化,以及东北草原深沉而凝重的多民族原生态的强者基因,更是书写了强者基因力量给后代人们带来的潜在希望……同时也在呼唤着生态文明,呼唤着日益萎缩的东北草原,呼唤着不断远去的霍林河水和早已溃散的草原狼群……
《血色草原》确实讲述了很剽悍的故事。讲述了渔猎农牧家族乃至整个东北草原从兴到衰,又从衰到兴的艰难演变历程。以查干淖尔大草原霍林河畔塔头滩上王氏和胡氏两个家族兴衰为主线,通过对王氏几代弱民呕心沥血执着争当强者、争当英雄艰辛历程的描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铮铮铁骨、不懈追求的草原人物。尤其塑造了面对苦难天性乐观,永不言弃,刚柔并蓄的祖母这个独特形象,充分展现了东北草原人的生存状态和别样性情。不仅是王氏家族的百年生存梦,更是王氏家族充满血泪的百年英雄梦。
我一直喜欢写“人物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喜欢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近年来,我侧重于生态链挖掘和小人物塑造,继《公鸡大红》、《小鸟在歌唱》之后,我还创作了《叔恩浩荡》、《谁都想好》、《别来无恙》和《月亮作证》等中短篇作品。包括我正在创作的《邻有养狗者》《沉默是金》等中短篇,也都是在描述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令人无奈的欢快与伤痛。谁都想好,可是有时好起来真的很艰难。
2018年的秋天和2019年的夏天,我两次参加中国作协主办的国际写作营活动,又两次近距离地审视了家乡草原,使我对家乡草原的认识又有所提升。去年,我还在冬天来到了查干湖畔,又体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冬捕场面……终于在2020年10月,我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第十二稿。
长篇小说《血色草原》虽然题材不同,但是好像也在传达着同样的感受和信念。由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1998年的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面对生活中很随意的一个突发情件,人类都显得过于渺小了。好在人类的精神生活往往能通过无奈的现实而变得丰满起来,支撑着幸存者继续走下去,以实现生生不已的态势。
在此,由衷地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和吉林省作家协会的大力扶持,感谢《中国作家》杂志社和作家出版社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厚爱。同时,还要感谢为这部作品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编辑老师和评论家们,他们都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
2021年1月26日改定于长春听溪阁
王怀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编审。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库专家,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在《中国作家》《十月》《作家》《钟山》《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期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风吹稻浪》《芬芳大地》等七部;出版小说集《谁都想好》《小鸟在歌唱》等八部;另有《春去春又来》《我那遥远的红草原》《叔恩浩荡》等戏剧、电影、散文作品若干。作品荣获梁斌小说奖、田汉戏剧奖、冰心散文奖、吉林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等奖项。三十余次被国内选刊选载和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和精选本,短篇小说《公园里发生了什么》入选大学生阅读教材,还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韩等文字介绍到国外。